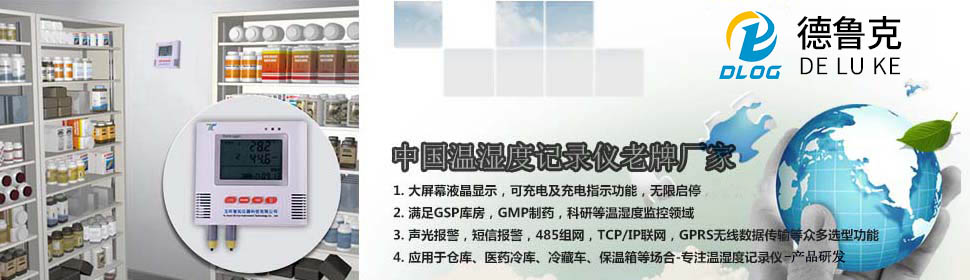孫保全 潘冰冰:中國邊疆研究不應盲從西方理論
近代以來,**邊疆研究先后掀起以西北史地學、邊政學、邊疆學為標志的三次**。這一發展過程,始終伴隨著西方邊疆理論的傳播。西方邊疆理論固然有值得借鑒之處,但也存在需要警惕的謬誤和缺陷,特別是擴張性價值理念、多元化視角和解構性話語,對**邊疆研究乃至**安全,產生諸多消極影響。
擴張性價值理念挑戰和合文化底色
西方的邊疆觀念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期。羅馬人通過戰爭不斷向外擴張,逐漸形成帝國的邊疆和邊疆制度,并且產生描述邊疆的專門詞匯。近代早期,歐洲的民族**在確立主權體制進而形成領土邊疆的同時,通過重拾歷史上羅馬帝國對外侵略擴張的手段,建立與古代殖民地邊疆相呼應的近代殖民地邊疆。正是從這一時期開始,西方邊疆理論形成并發展起來。從法國為實現大國霸權而對“自然疆界”論的不斷強調,到德國地緣政治學創始人拉采爾基于**有機體理論而論述“作為邊緣機體的邊疆”,到美國歷史學家特納以“自由土地”與“移動的邊疆”為基礎提出的“邊疆假說”,再到英屬印度出現并經由寇松等人系統論證的“科學邊疆”概念,西方邊疆理論無不充斥著擴**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隨著殖民體系逐漸瓦解和新獨立**大量涌現,領土邊疆成為主導性邊疆形態。在無法通過大規模侵略擴張來實現邊疆開拓的情況下,西方**開始圖謀構建超主權領土的新形態邊疆。20世紀60年代,美國政府提出“新邊疆”政策,將“尚未涉足過的科學與太空領域,尚未解決的和平與戰爭問題,尚未征服的無知與偏見的角落,尚未解決的貧窮與過剩的問題”,通通納入“邊疆”范疇。受此鼓動,“高邊疆”、“利益邊疆”、“戰略邊疆”、“信息邊疆”等一系列超主權邊疆觀念始漸大行其道。這些所謂新形態邊疆觀念及相關論述,皆服務于美國全球霸權。
鑒于擴張的歷史傳統,西方邊疆理論及其指導下的**邊疆歷史研究,自然不免“以西律中”,對**邊疆歷史乃至現實邊疆政策充滿偏見。在不少西方人看來,古代**是與羅馬帝國相似的**形態,并以西方的“帝國”概念為內核,建構所謂“中華帝國”概念,作為研究**邊疆的邏輯起點。這一研究范式萌生于16、17世紀的歐洲,19世紀后期傳入**,后經過西方漢學家反復使用,成為所謂“不言自明的常識”。200多年前,魁奈就在《中華帝國的專制制度》中想當然地為**劃出一個“疆域范圍”:東臨東海,北抵長城,西接沙漠,南至海洋,今天的東北三省,內蒙古、新疆、西藏三個自治區,以及云南等邊疆地區都不在所謂“中華帝國”之內。進入21世紀以后,西方學界提出“新帝國史”理論,將視線轉移到“大清帝國”上,把漢族與少數民族、**與邊緣**對立起來。以上兩種關于**的“帝國”論,雖有“新”“舊”之分,卻無本質之別。照此邏輯,**的邊疆地區是“帝國”“征服”的產物,是處于所謂“**本部”之外的殖民地。
以“帝國”論框套**歷史的做法,對**的影響已非一日。自清末起,**人自稱帝國的現象就開始出現,嗣后將秦、漢、唐、元甚至西周稱為“帝國”的話語逐漸流行。新**成立后,類似說法在大陸學界銷聲匿跡,但隨著海外**研究作品大量譯介,所謂“中華帝國”又在大陸學界乃至**界卷土重來以至泛濫成災。有人把“帝制”**等同于“帝國”,懵懂地接受所謂“中華帝國”概念;有人則自覺不自覺地“擁抱”這一話語及其背后的研究范式,將以融合為主旋律的**統一多民族**形成發展過程,視為以中原為**的所謂“帝國”對“邊疆”的“吞并”和“征服”。
如果說“帝國”論導致了對邊疆歷史的歪曲,那么“地緣”論則導致了對邊疆現實的誤判。近代以來,以麥金德陸權論、馬漢海權論、杜黑空權論為代表的地緣政治學說陸續傳入**。**一些研究者夸大地緣政治學的意義,將此作為闡述陸地邊疆、海洋邊疆、空中邊疆、太空邊疆的理論基礎。聽聞美國人提出“利益邊疆”、“戰略邊疆”概念,一些人呼吁**應趕上潮流盡快構建新形態邊疆,更有甚者,視“海外利益攸關區”為**的“利益邊疆”,將“一帶一路”建設理解為**“利益邊疆”的開拓活動。西方地緣政治學雖偶有對**邊疆的零星討論,但并非嚴格意義上的理論,而“利益邊疆”、“戰略邊疆”等時髦詞匯,只是西方**有關地緣政治戰略的一種空間隱喻,更不用說無論是地緣政治學,還是由地緣政治戰略引申而來的新形態邊疆觀念,都傳承著西方文化的擴**因。
與西方邊疆歷史和邊疆理論暗含的擴張主義價值不同,**邊疆觀念的價值底色是強調和諧、和平、合作的和合文化,植根于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歷史上歷代王朝采取“撫之以仁義”、“懷之以德”、“修文德以來之”以及“因俗而治”的治邊方略,今天黨和**實施新時代興邊富民行動、開展邊疆地區對口支援、構建**與周邊**命運共同體,和合的價值觀始終如一、一以貫之。
多元化擾亂整體疆域視角
**是世界上最早建立邊疆管理制度并實施邊疆治理的**之一。**古代雖然沒有專門的邊疆學科,卻有著豐富的邊疆學問。在古代文獻中,“邊疆”、“邊陲”、“邊地”、“邊圉”、“邊境”、“邊徼”等用語名異實同,均用于指稱邊疆。《國語》中“夫邊境者,國之尾也”的記述,就是古人對邊疆的理解。晚清**時期,邊疆空間性質發生主權化轉型,國人開始以**領土來界定邊疆,強調其有異于核心地區的特性。在今天的各類文獻中,邊疆被解釋為靠近邊界的區域或地帶,具有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方面的特殊含義。盡管**人描述邊疆的具體方式存在古今差異,但認知視角保持著一致性,即立足整體疆域看待邊疆,將邊疆視為疆域的組成部分。
以整體疆域認知邊疆的視角,源自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和“大一統”傳統,而西方文明沒有“大一統”傳統,更不具有突出的統一性。西方學者傾向于從多元化視角認識邊疆。多元化視角肇始于美國歷史學家特納。他在1893年發表的《美國歷史上邊疆的重要性》一文中,將白人殖民定居地定義為“文明”,將原住民生活地區定義為“野蠻”,美國陸地邊疆的擴張移動則意味著“文明”對“野蠻”的勝利。相比特納的美國邊疆假說,拉鐵摩爾關于**邊疆研究的影響更為直接。1940年,《**的亞洲內陸邊疆》在美國出版,次年中譯本便在**發行。當前對拉鐵摩爾本人及其邊疆理論的討論仍呈現方興未艾之勢,可見其影響之久之深。雖然拉鐵摩爾與特納關注的對象不同,但認知視角一脈相承。與特納的二分法相似,拉氏將**疆域劃分為兩部分:一是長城以內的18個省,被其視為歷史上的“**”;二是長城以外的“滿洲”、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則從屬于“亞洲內陸”。拉鐵摩爾認為,在“亞洲內陸”的“草原環境”與“**環境”之間,存在一個過渡地帶,而邊疆就形成于這一過渡地帶。在此基礎上,拉鐵摩爾劃分出“內外”邊疆,靠近草原游牧社會一側的區域是“外邊疆”,靠近中原農耕社會一側的區域是“內邊疆”。簡言之,拉鐵摩爾眼中的邊疆是“**”與“亞洲內陸”之間的過渡地帶,而東北、內蒙古、新疆、西藏等地區是與“**”相對的“亞洲內陸”。拉鐵摩爾之后,“內亞—**”視角在西方學界繼續發展,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與**》和狄宇宙《古代**與其強鄰:東亞歷史上游牧力量的興起》是典型代表。類似視角還被應用于**西南邊疆研究,自從斯科特炒作所謂“贊米亞”概念,強調**西南地區“東南亞性”的讕言便不絕于耳。
所謂多元化視角的研究路徑是,先按照文化、地理、民族、經濟等分野劃出不同類型的區域,再通過區域間交互關系來界定邊疆。在整體疆域視角下,邊疆的核心要義是“邊緣性”;在多元化視角下,邊疆的空間特征是“過渡性”,也就是不同區域之間的過渡地帶。此外,整體疆域視角在**統一框架下界定邊疆,視邊疆為**疆域的一部分;多元化視角定義的邊疆則不以**為參照,有時干脆置邊疆于**之外,因而多元化往往走向“去**化”。西方邊疆理論對**邊疆歷史領域的滲透,致使兩種截然不同的概念雜糅在一起,原本清晰的邊疆含義變得歧義重重。
在西方多元化視角影響下,**部分學者自覺不自覺地接受**北部邊疆具有所謂“內亞”屬性和西南邊疆具有所謂“贊米亞”屬性的理論預設;另有人將多元化視角視為打破“中原**主義”的“創新”,使得**早已達成共識的基礎理論,反而成為所謂被“超越”的對象。關于如何認識**歷史疆域的問題,**學界在20世紀50年代和80年代有過兩次大討論。白壽彝與譚其驤先后作出的論斷,即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或清代前期的疆域來確認歷代版圖范圍的方法獲得學界普遍認可。后人在此基礎上談論邊疆,并未在空間維度上出現過明顯分歧。盡管近代以來也有過政治邊疆、文化邊疆、經濟邊疆等多種說法,但這只是在原有空間基礎上對邊疆其他屬性的豐富和補充。而在所謂多元化視角下,**邊疆的面貌變得晦暗不清,被附會上本屬于西方邊疆的過渡性和移動性內涵。而過渡性和移動性又會推導出邊疆歸屬的“不確定性”,隱含著動搖**整體疆域視角的風險。
解構性話語沖擊“大一統”敘事傳統
西方邊疆理論中擴張性理念、多元化視角**體現為具體話語,當使用這些話語來描述和闡釋**邊疆歷史時,便表現出解構歷史**的傾向。在**東北邊疆研究領域,西方邊疆理論話語中的“滿洲”一詞,帶有片面突出所謂“多元性”的意涵,如謝健《帝國之裘:清朝的山珍、禁地以及自然邊疆》就著意區分“東北”和“滿洲”。對于北部邊疆,西方人先是將其歸入“中屬**”,后又列為“內亞”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一些國外學者仍然不愿意將內蒙古自治區視為“**古代北疆”,最多只承認內蒙古中南部“長城地帶”是**古代邊疆。對于作為西北邊疆地區的新疆,米華健等人罔顧清朝在西域設省時所取“故土新歸”之意,而有意將其曲解為“新的疆域”,以突出所謂“殖民地”屬性。在西南邊疆方面,《劍橋**晚清史》把19世紀的西藏視為擁有“領土”、“**政府”的“**”;云南的情況更為復雜,在百余年時間里,或被裹挾進“泛泰主義”思潮,或被定義為“**、法屬印度支那和緬甸之間的地理邊疆”,或被納入所謂“大陸東南亞”、“曼陀羅體系”、“贊米亞”等范疇。
除了空間話語,西方學者在研究**邊疆時,還制造并使用一系列解構性話語。西方學界長期誤讀曲解中華文明的**形態,將“大一統”與“帝國主義”混同,把“中原”指為“**”,以“擴張”、“征服”、“侵略”、“殖民”等話語表述內地與邊疆的關系。隨著“新清史”興起,一些西方學者把清朝從**歷史中剝離,將中原連同蒙古、西藏、新疆等邊疆地區一并謬認成清朝“殖民地”。當前,這套話語模式不僅被用于討論陸地邊疆,還用于海洋邊疆;不僅被用于討論古代邊疆,還用于當代邊疆;不僅被用于解讀正史,還用于解讀方志。比如布琮任《海不揚波:清代**與亞洲海洋》提出“海洋帝國性”概念;戴思哲《中華帝國方志的書寫、出版與閱讀:1100—1700年》把編纂邊疆地區方志歸因于“將未同化地區納入帝國之內”。
除解構**邊疆空間整體性和歷史連續性以外,西方人還臆造并運用大量民族主義話語。將民族同地理結合在一起的觀念,發端于歐洲民族**的構建。西班牙人文地理學者胡安·諾格認為,“‘民族領土’觀念,是一切民族主義的根基”。照此思路,西方人把**疆域強行分割為“漢”與“非漢”的二元世界,稱中原地區為“漢地”、“漢人**”或“**本部”,意為漢族專屬土地。在此基礎上,一些西方著作給不同邊疆地區一一貼上相應的族屬標簽。例如,歐立德《滿洲之道:八旗與晚期中華帝國的族群認同》妄稱“滿洲”是一個民族性術語;璞德培《**西征:清朝對**歐亞的征服》使用“**厥斯坦”的表述;《劍橋**晚清史》把“西藏本土(部)”看作“****的國度”;**《流動的疆域:全球視野下的云南與**》以“漢”與“非漢”人口比重為標尺來衡量西南邊疆的“**化”進程。于是,各民族共同開拓**疆域以及**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史實,就被扭曲為不同民族之間的征服、殖民、侵略和滅絕。
然而,當下**學界和**界對上述問題仍有麻木不仁甚至深以為然者。網絡上時有學舌“崖山之后無中華”的雜音,學界還存在使用“**本部”的亂象,也不乏為“新清史”“正名”者。殊不知,近代帝國主義侵略者就曾以“**本部”、“長城以北非**”、“滿蒙非**”等話語作為**、侵略**的工具。新**成立以后,“**少數民族地區為**之外”的訛言仍為別有用心者利用。今天,國外**勢力反復炒作涉疆、涉藏謊言,一些所謂“價值中立”的西方學者在其中扮演了提供話語武器的角色。
西方的邊疆理論誕生于西方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西方的漢學或**學,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門將西方的價值立場、學術視角、歷史經驗施加于**的“學問”。因此,對待西方學界的邊疆理論和涉及**邊疆的話語,需要保持一種自覺意識,既不能一概否定,更不能一味盲從。所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意在以他山之石成就本山之玉,而不是棄玉就石、是他非己。盲從西方理論,相信“外來的和尚會念經”、“外國的月亮**圓”,輕易放棄自己的理論積累,終將喪失文化主體性,陷入邯鄲學步、非中非西的尷尬境地。
本文 軟文網 原創,轉載保留鏈接!網址:/news/73678.html
1.本站遵循行業規范,任何轉載的稿件都會明確標注作者和來源;2.本站的原創文章,請轉載時務必注明文章作者和來源,不尊重原創的行為我們將追究責任;3.作者投稿可能會經我們編輯修改或補充。